710万研发人员多是普通人才,中国怎样成为世界科学中心?-米乐体育官方下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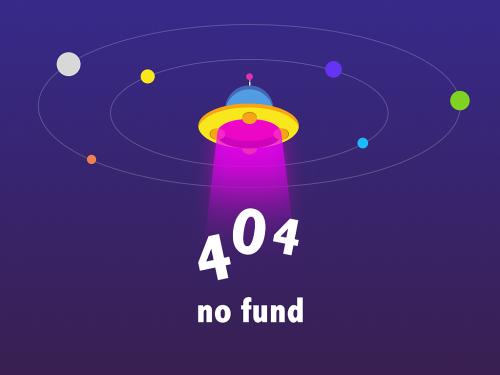
郭传杰,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。(摄影 | 王峥)
1.跟踪模仿成了习惯
怎么建设科技强国?
问:我们国家提出在建国百年的时候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,尤其当前我们面临国际上的卡脖子形势,您怎么看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性?
答:我们中国经济的体量是很大,我们科学界发表的文章数量也很大,但是要知道,强和大是不一样的。
什么叫做世界科技强国?当你真正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了,那才叫强国。这不是看你的经济体量有多大,不是看你能做出多少从1~100的东西,你必须要有自己原创的东西,也就是要有很多从0~1的突破,你有的别人还没有,这样你才能够称得上强,如果别人有的你才有,充其量是跟着人家后头,你就强不起来。
我认为所谓的原创,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东西:科学上的原创,技术上的原创,还有产品级的原创,这三个层面如果我们都有原创性突破,科学中心、产业创新高地,就会形成,那就强起来了。但是,我们现在无论哪一个层面,原创都很不够。
这是近年国家不断加强科技原创工作的缘由。特别是从2018年后,美国卡我们脖子的,第一批清单就涉及了30多项,这需要我们一个个去解决。要从基础研究方面加强,不能只是被动解决卡脖子问题。科学原创上强了,将来我们才有能力去卡对手的脖子。
问:其实被卡脖子也促使我们反思:为什么我们做不出很多原创性的一流的研究成果?
答:是的。为什么缺原创?产出原创性成果,得有两个前提:一流人才和创新文化。文化更带根本性。一个社会如果不重视原创文化,只习惯于跟踪模仿,不可能出一流的原创成果。
近代几百年以来,我们中国基本上都是在学习跟踪发达国家。改革开放这40多年,是我们学习跟踪最好的一个时期。的确,我们是得到了发展,但是温水煮青蛙,慢慢成了惯性,也渐渐忘记了创新。
我们过去做科研,要立一个课题,先要做各种文献调研,没有3、4个月是不行的,要看很多很多文献资料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,我的教授快60岁了,他40多岁就是美国科学院院士,那天亲自开车到车站接我。刚上车,就问我:“传杰,你准备开个什么题?”
我说得先做一下文献调研。他说你要多长时间?我想在国内是几个月,在美国肯定不能那么长,我说,一个月吧。他当时感到很惊讶:做文献调研要用一个月?我问多少天合适?他说最多就两天,最好是一天。
我大惑不解。他说,你就看看我们group(组)在做的工作就行了,别人的你看它干什么?我们就在最top,处在最前沿,别人的没必要去看。
我事后想,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整个都是这种氛围,做任何一件事,总是要先花好长的时间看看别人做没做、怎么做,形成了习惯性的不自信。包括863计划,开始提出的目标也是要 “跟踪” 世界高技术,在当时敢于提出这个目标已经很不容易了。长时间在这种文化下搞研究,很难顺利地切换到原创上,所以,我们需要有一个深刻的文化变革才行。
2.缺少一流顶尖人才
难有重大的原始创新
问:讲到创新,关键需要人才,我们在人才方面,储备够么?我们人才的水平处在什么层次?
答:我们中国人,智商不差,全世界公认最聪明的一个是犹太人,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。但真正原创性的重大科学技术创新,往往不是一般的聪明就能够做出来的,只有一流杰出人才才能做出来。
从数量上看,我们人才队伍是很大的,据科技部2020年的官方统计,rd(研发)人员已经达到710多万,规模世界第一。但是我认为,其中大量都是普通人才,以二流、三流的人才居多,一流的人才,就是钱学森钱老所期待的那种人才,我们还是很缺少的。
当然,我们不能否认普通人才的作用。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其大多数都是这些普通人才完成的,包括今天的许多科学技术进展,很多科研论文和专利。但是,重大独创性的东西不多,这是事实,是个很严峻的问题。
问:既然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,为什么我们就出不了钱学森所说的那种顶尖人才,甚至是天才?
答:2005年7月,钱老和总理谈话时,原话是 “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,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,老是 ‘冒’ 不出杰出人才”。这个 “冒” 字大有文章!你说,为什么我们出不了钱老说的那种顶尖人才?我觉得这跟社会的整个文化环境和人才培养机制有很大关系。真正一流的人才往往受到抑制,不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。为什么?

图1 1995年在钱学森先生家中拜访(左起:宋健、温家宝、钱学森、蒋英、郭传杰)| 受访者供图
一流杰出人才往往有几个特点,一是思维深邃,如爱因斯坦擅长哲学思考,马斯克考虑问题爱遵循所谓第一性原理,都有很强的洞察力,能直击问题本质。
二是敢于求新、试错,敢为天下之先;
三是个性突出,独立特行,习惯质疑,不大听话,与世俗价值观合不来,甚至身上有刺,头上有辫子,总之不是乖孩子型的。
一流人才和普通二、三流人才的差异不是量上的、程度的不同,不是90分与80分那种区别。十个、百个普通教授加起来也不能等于一个牛顿或马斯克。一流学者带来的是新方向、新观念、新技术的质变。
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,更讲中庸之道,做人的智慧,对那些特别有个性的人,就是不打击你,也有可能被另眼相看,同路人少,比较孤独、孤立。一旦表现冒尖,成为出头之鸟了,就有挨枪子的危险。为什么要杀一儆佰、枪打出头鸟?大家就安分了,服管了呗。这种文化,对那种特别有天分的人才,就不够宽容和包容,自然就 “冒” 不出来了。
所以,我认为,二流、三流的普通人才,是可以大批量培养的,就像全国这些年来的各种 “人才工程” 那样。但真正一流的杰出人才,如乔布斯,是谁培养的?好苗子是好种子在土壤肥沃、雨顺风调的环境下,自己 “冒” 出来的,这个环境就是常说的创新生态和文化。
问:多年以来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,为什么很多华人科学家在国外的土壤中能够很快成长起来,拿到诺奖,做出一流的科研,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?
答:科学上的创新,要把个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,要敢于质疑,敢于探究,敢于打破各种框框的限制。
长期以来,我们基础教育的基本逻辑是:在学校,学生把老师教你的知识点都记好了,老师按讲的知识点出考题,你按标准答案都答对了,考试就拿100分。这样,你当学生的就是好学生,我做老师的就是好老师,教育的过程走到这里就到此为止,皆大欢喜。
但真正好的教育,就是这样的吗?不是的。教育走到这里,还只走了一半,还有循环的另外一半。而这一半我们还没走。那是什么呢?
譬如说,你是二年级学生,你已经掌握了我教的课本知识,但你还得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,你得有新想法或者好奇心,如果你提出的问题连我当老师的都答不上来,这才是好学生。为什么?你有创造性了,你有再创造新知的意识和能力了。而我,不断引导你提出好的问题,我才是好老师。
想想看,如果在学校里学生都没有思维习惯,没有认知能力,不能提出问题,只是会考高分,上好大学,把这当成是教育的唯一目标,那一流人才怎么能出得来?

图2 1996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振宁办公室座谈(左起:杨振宁、陈宜瑜、郭传杰、郝柏林)| 受访者供图
3.没有良好的文化
有人才也难以发挥作用
问:讲到原创文化或创新活力,我特别想请问,同样是亚洲国家,日本为什么在这方面表现突出?日本出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,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?
答:就整个社会层面讲,我认为日本绝不是一个创新文化的国度。他们原来军国主义味道是很浓的,他们的文化讲服从性,部队里三等兵要给二等兵打洗脚水,二等兵给一等兵打洗脚水。走到电梯门口,碰到主管、领导们,你得站在边上让他们先走。
但是日本最近这20年里,平均每年能出一个诺贝尔奖,目前已经19个了。涌现这么多一流科技创新人才,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?
我认为他们有点类似于搞科学特区的做法。就是对某些领域和机构,政府给他们特殊政策,就像我们当年在深圳沿海地区搞经济特区一样。日本在二战之后,很快着手修改他们的教育法,向西方国家学习,挑选了东京大学、京都大学等7个大学,给它们高度的办学自主权。政府的文部省只给学校经费,不具体去管,学校基本上是学术自治。这些做法一下子就把大家的创新力激活了。
经过几十年发展,到这个世纪初,他们当时有一个规划,说是在50年里要出30个诺贝尔奖。消息一公布,我们都笑话他们:诺贝尔奖你也能够规划出来?没想到,后来真的出现了诺贝尔奖井喷现象,近20年他们的得奖人数仅次于美国,超过了欧洲国家。他们的成功,除了足够的经济保障外,更得益于他们让学术机构完全按照学术规律办事,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借鉴的。
一般企事业单位、军政部门,强调执行力是应该的,但在科学上,就不应该强调执行力,而是要尊重创造力和创新力。如果把那种服从性的文化拿到科学研究上面来,那就错位了,必然压抑创新。
对于科研工作,我觉得要特别强调因人、因工作的不同而推行差异管理,要有不同的方式和文化。因为,人才是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,要有不同的标准,管理上笼统一刀切,绝对不可取。
问:您是不是不主张给科学家加任务,说我要给你设定一个kpi,我要给你很多很多的考核指标,让你围绕这个kpi来做科研,就像我们在公司工作一样,每个季度给你kpi考核,不合格扣奖金,你晋升不了,科研创新肯定不能这么搞,对不对?
答:如果你想扼杀一个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,你可以不断给他布置各种kpi,不断去考核他。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,但它完全违背了科学创新规律。其实对任何创新性、创造性的工作,都不宜用这种办法管理。
尤其是,以探索性、原创性为主的科学研究,是面对未知的,你怎么给他布置任务?当然没必要这样去考核他。你要做的是选好人、选对人。一流的人选对了,你就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,给他稳定支持,放手让他去探索、做事。你不用问也不用催,他自己会有一种内在的motivation,就是内在的驱动力。不是因为你给他任务他才去做,也不是为了得诺贝尔奖去做,更不是为了发文章去做,他这一生就是为了解决感兴趣的科学问题,活着就要去探索其中的奥妙。这样的人你怎么给他定任务,你为什么要给他定任务?你就给他配置好的条件,由他去自由探索,就行了。
二战时期美国科学院一位院长说过,创造性工作是人的心智运作的结果,思维之花在最大自由的氛围中盛开。没有人事先能预言别人头脑将会想什么,也不能强迫人们产生新的思想。作为管理者,唯一能够做、应该做的是,给他们提供必要条件和良好环境。
我们现在的科研管理工作还做不到这样。我想强调的是,希望我们在原创科研的管理上,能更宽松些,更人性化,别那么急功近利。
问:讲到急功近利,因为现在处于商业化大潮中,很多东西都被物化了,大家想的都是怎么能快速赚钱,怎么快速产出,太缺那种静心坐下来思考和研究问题的风气了,当人人都围绕着kpi打转,哪有功夫和精力去想着做些创造性的东西?环境也不容许你不慌不忙这样做。
答:企业管理,kpi是有效的。原始创新需要少数人,能静下心来去思考琢磨。比如说,现在都在用手机,那手机之后的下一个产品创新将会是什么?再比如交通工具,19世纪初德国人发明了自行车,我们后来引进自行车了;人家有汽车,我们也有汽车了;人家有了高铁,我们也就有高铁,可喜的是,我们现在高铁比人家还强一点;现在马斯克搞真空管道运输,我们现在也紧跟着搞。但我们怎么就没有一个超乎别人的东西,哪怕只是个想法呢?近几百年来,为什么就极少见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发现、发明,像先人那样,能为人类文明做点贡献呢?
这就是个文化环境的问题。社会要鼓励有人去琢磨,哪怕是胡思乱想,总比躺着不动,总比老是跟在别人后面强。
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,他们就有 “疯子基金”,你有个什么点子,哪怕是胡思乱想,给点钱让你去试(当然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),试了以后,只要不是弄虚造假,失败就失败了,在100个案例里边,如果有一个成功,可能就不得了。
自然科学基金当然应该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。比如说,面上项目,5个专家要4个同意,才获批准,少数服从多数。但如果你提出一个完全是超乎现有认知水平的、带着奇葩想法的一个项目,很可能得不到专家的共识,也就很难获得资助。因此,需要一个非共识项目的评审机制,以保护少数。
问:允许创新、包容创新、鼓励创新,让更多人放手去做,是不是也是原创文化的一个特点?我想到潘建伟院士,网上有很多对他团队的议论,您是中科大的老领导,您怎么看这个现象?
答:确实,我也注意到,网上常有些对潘建伟的流言蜚语,说什么 “骗钱” 啦,等等,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,应该怎么对待一流的创新人才?中国总有些人就是见不得你冒尖。
像美国的马斯克,(我不是说潘建伟和马斯克完全同日而语,马斯克目前当然更有影响力)两相比较,马斯克做的事情也失败过,火箭几次掉到海里,个人生活方面据说还有些非议。但他成功了,仍然能够把事情做起来。美国社会包容这样一些特立独行的人。
而在我们社会中,你某个人做得出色的,首先我就否定你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好,哪怕我不懂你的专业,我也要猜疑你。这时候,你如果心理上不强大,可能就退缩了,放弃了。
我记得十多年前,国内也有人说:中科大,你搞什么量子计算?电子计算到量子计算还远着呢!直到美国google也好,mit也好,都在做量子计算了,这时候才对发展量子计算少些异议。
据我了解,潘建伟他们团队,是非常优秀、有竞争力的,都很年轻。潘建伟自己就是1970年生人。他们进入到无人区,外国在探索,他们也在探索,当然可能有失败。其实,科研过程大部分是失败的,你只要是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,在科研道德的规范下,失败应该是允许的,甚至是应该支持的。因为,只有通过失败才能够走向成功。
何况,他们团队到现在为止,还真没有什么重大失败,世界上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,不是2016年就上天了嘛,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。量子计算机,他们独立研发了100多个光子体系的“九章”系列、60多个比特的超导型的 “祖冲之”,使我国成为目前唯一同时在两种物理体系都达到 “量子计算优越性” 里程碑的国家。国际学术界都承认,几次给他们发大奖,可国内还是有人不时地喷口水,真不可思议!
问:讲到教育,您是专家,是不是教育上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来一次变革,才有可能真正培养出钱学森先生所说的一流人才?
答:办好教育很重要。其实,人才是有多种多样的,前面说过有不同的层次,一流、二流的,此外还有不同的类型。教育如果用统一的尺度去衡量,统一的标准去管理,一定不会成功。因此,学校要有不同类型,多种多样。此外,我们的教育不是培训工具,而是要培养人才,这个理念很重要。
你看普林斯顿、哈佛、mit、斯坦福等世界名校,每个学校都有自身很强的特色,学科的设置不一样,人才的培养目标也不一样。耶鲁大学的老校长莱文说,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毕业后,居然有某种很专业的技能,就是耶鲁教育的失败。这句话,用在耶鲁,当然对,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领袖型人才。但是,这句话适合于所有的大学吗?答案是显然的。
如果是一个职业型的学院,当然要培养专业型人才。整个社会总是需要各种类型、不同专业的人才,学校得多元多样,各有特点特长,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。
另一个问题是,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,这一点我们行吗?我们不行,差得远。
“双减” 之后,社会上的补习班乱象是少多了,但学校教育还有很多问题。翻开学生的课本,有不少前沿的知识,但多是把它作为孤立的知识点来展现,让学生记忆,不告诉学生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,没有来龙去脉的过程分析。辅导书、考试卷再加上更高年级的知识点,所以学生负担没减,疲于记忆,学得不活。教育改革是整个体系性的改造,各个环节都得跟上,所以路还很长。

图3 2004年在中国科大调研少年班老师阅卷 | 受访者供图
4.中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可期
但具体时间不好说
问:有一个观点说,美国科学强大是因为二战的时候,像爱因斯坦这样一批大师移民到美国去,人才汇聚起来,全世界的人才能为他们所用,才带来了科学的繁荣,您认同这个说法么?
答:这个观点当然有道理。当时一大批知名科学家从德国欧洲去到美国,美国当时的经济正处在上升时期,有足够的经费支持,美国本土的人才和外来的科学大家相结合,当然对美国科技的强大有推动作用。
但我想,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。还有个社会机制和文化问题。试想,当时的美国如果是一个压制人才的机制和文化,这批人才就算去了,你爱因斯坦去了,能发挥大作用吗?像纳什这样的科学家,多少年不出工作成果,解决费马大定理的那位老兄(著名数学家安德鲁·怀尔斯),10年一篇文章都没写,他们仍然可以愉快自由地呆在普林斯顿,因为那里有这种包容性的宽松氛围。
如果对你每月一小考,一年一大考,业绩不够就末位淘汰,你还能在那里呆得下去?所以,根本的问题,还是跟人才机制、学术生态有关,要有适应学术发展的文化土壤才行。
问:有一种说法认为,世界的科学中心不断在转移,比如之前是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,现在有些人很乐观,相信这个中心之后会向东方转移,您认同这种看法么,这个中心在向东方转移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讲有没有可能向中国转移?
答: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,在地球上发生时空转移,这是个历史现象,具有规律性。近500年来,已发生过5次。最早在意大利,文艺复兴带来了近代科学的启蒙。接着转移到英国,发生了工业革命。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使法国迎来了第三次科学中心的转移。再后来,转移到了德国,重化工、冶金、电力等领域发展起来了,德国西门子就是创立于1847年的老店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发生第五次转移,到了美国。直到目前,美国仍是世界的科学技术中心。
接下来该往哪里转移?主观愿望上,我们当然希望下一站就是中国,客观上,可能性也很大。据统计,2021年我国大陆的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,居世界第一,其中高被引论文数量和热点论文数量均居世界第二,仅次于美国。2021年专利申请量也是世界第一,超过了美国。
还有一个视角,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趋势,也可以看到一些趋势。过去几百年来,科学技术是不断走向细分化。科学分成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等,化学再分为无机、分析、有机、高分子、物化等等,再分成三级、四级等,越分越细。现在,学科的交叉、交融、综合,成为了更重要的趋势,这正好跟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特点比较合拍。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比较重视系统、较综合的,跟西方的分解式思维不同,这也是认为科学中心将往中国转移的一个依据。
不过,有人判断世界中心马上就要到中国了。我觉得可能太乐观,具体时间不好预判。因为,历史上,科技中心的转移与经济中心、教育文化中心是相联系的,但这三个中心的转移不同步,其间还有时间差。
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中心,就要有培养一流创新人才的教育,要吸引世界上最强的科学头脑,要有吸引人才的创新文化,还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,完善的创新链、产业链,这些要素综合起来,基本具备了,世界科技中心就会水到渠成。
问: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科学正在衰落?或者说他们会衰落吗?
答:前两年,网上讨论过这个问题,有不少人持 “美国正在衰落” 的观点。著名学者谢宇(美国科学院院士、普林斯顿大学教授)与人以《美国科学在衰退吗》为题合著过一本书,其观点认为,现在美国的科技进步虽有减缓,但还没有衰退。他们的立论是基于对一流人才、一流大学以及社会的创新机制和文化等的综合分析。
你问我的看法,两点:一是从论文、专利、科研经费等统计数据来看,毫无疑问我们的发展速度和势头都处于世界领先位置,但对科技发展的评价,不同于其它领域,还得考察某些更深层、复杂的要素。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。
二是从发展趋势看,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它的客观规律,要经历新生、成长、衰亡若干阶段,这个辩证法,谁也逃脱不了,一个人活到100岁,即使还健康,也总是要衰亡的。当今世界,我们中国是在往上走,他们是从顶峰往下走,这是个基本趋势和事实。当然,我觉得外交部发言人有句话说得好:我们的目标是要不断地超越自我,并不是要谋求某天去超过别人当个老大。当然,未来的趋势是注定了的。